热点新闻:
现在是:
首页 >艺术家风采 > 内容
兰州市戏剧舞蹈家协会会员(编剧)推介——董雄鹰
兰州文联网 时间:2025-07-0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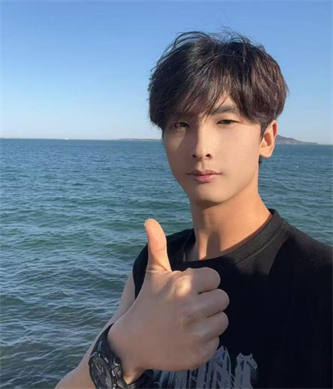
现就读于兰州文理学院,兰州市戏剧舞蹈家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曾获甘肃省第十八届海州杯二等奖、黄河流域三等奖等,个人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等。

秦腔《打镇台》中饰王震
秦腔《禁烟轶事》创作谈
第一次在图书馆翻开林则徐的传记时,我像发现宝藏的孩童,满脑子都是虎门销烟的烈火、百姓欢呼的盛景。我迫不及待地铺开稿纸,想写一部气吞山河的“禁烟大戏”。可当剧本写完第一场时,笔尖突然锈住了——那些精心设计的“忠奸对决”“万民请愿”,像一锅煮沸的鸡汤,香气扑鼻却无血肉。原来,初学者的狂妄,是对历史最深的无知。
不甘心的我转向“小戏”尝试,聚焦一个家庭故事。林则徐是顶天立地的神,吴三是被感化的浪子,李氏是深明大义的贤妻。在第二稿中我竟让吴三跪在钦差面前痛哭流涕,发誓戒毒后追随林大人扫清烟馆,仿佛一腔热血就能涤荡百年污浊。”最后林则徐以简短的四句唱就草草结束。当我把剧本给导师看时,老师问到“鸦片若这么好戒,大清怎会亡国”,而且民族英雄的形象塑造成了报幕的,在舞台上无所事事。回去继续查阅资料,当我看到“遂以烟膏灌其口毙之”时猛然醒悟,让吴三“励志”的结局不过是用糖衣包裹腐肉,比鸦片更毒。
在这一段时间,我成了自我折磨的苦行僧。吴三的结局是最大的心结,吴三的结局改了十几稿:他戒过烟,逃过荒,甚至加入过义军,但每次排演都像在糖水里泡黄连,甜得虚伪,苦得不痛。想到诗人痖弦的句子:“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,推敲起来,全是人骨头。
于是打翻了让吴三“浪子回头”的结局,写他烟瘾发作时,反复想象毒瘾噬骨的痛楚,那句“初尝之时似神仙”沾满了泪渍。吴三在儿女的哭求中烟瘾发作,当他最终跳河自尽时,那一瞬,仿佛亲手将角色推下悬崖,却听见深渊里传来历史的回声。也想到是不是太残忍了!”尤其是写豆豆和盼盼跪求父亲戒毒的唱词时,数次说不出来的难受。孩子的天真与苦难形成的反差,直指人性最柔软处。我不断自问:这样的痛苦是否有必要赤裸裸地呈现?最终,我选择相信观众——唯有直面血泪,才能铭记教训
林则徐的形象同样需要突破。传统戏曲中的清官多为“高大全”,但我希望他更像一个“人”。于是设计了他脱下官袍、深夜探访民间的细节。当他面对吴三的死亡时,那句“人志不可摧”不仅是劝诫,更像是对自己的叩问——在腐朽的官僚体系中,个人的意志能否真正拯救苍生?这种无力感,是我赋予角色的私心
作为西北人,选择秦腔并非偶然。它苍凉的哭腔、爆裂的梆子声,恰似鸦片烟瘾发作时的嘶吼。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,却让现实主义的痛苦表达屡屡受缚。李氏痛打丈夫的戏,让抓住棍棒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”。当李氏一棍砸向吴三时,台下观众竟下意识闪躲——那一刻,我知道,虚与实的界限终于被击穿。
唱词的打磨更是呕心沥血。林则徐的“眼见得”排比句,初稿略显冗长,但几番删改后,我决定保留这种“铺陈”。因为鸦片之害本就是层层累积的灾难,唯有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,才能让观众感受到窒息般的压抑。
《禁烟轶事》的创作,于我而言是一次心灵的刮骨疗毒。那些深夜伏案的时刻,我仿佛与吴三、李氏、豆豆一同在鸦片烟雾中挣扎。但正是这种痛苦,让我更坚信艺术的力量——它不必提供答案,只需唤醒凝视深渊的勇气。
剧本落幕时,林则徐的誓言仍在回荡,而吴三的尸骨早已沉入河底。这或许便是历史的真相:光明与黑暗永远并存。

剧照《禁烟轶事》